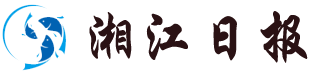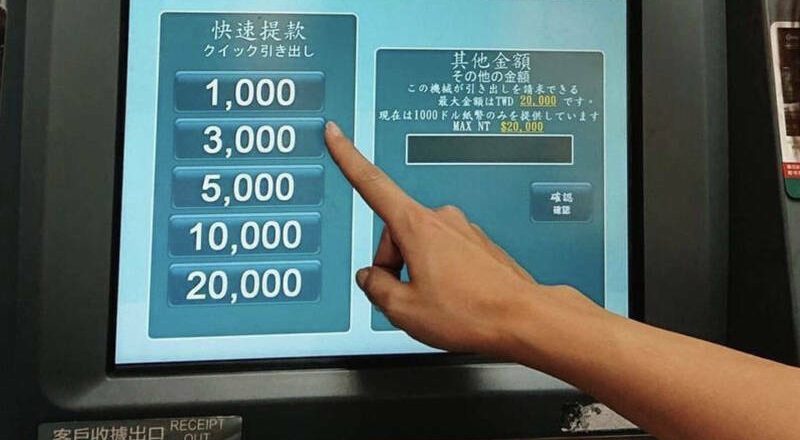自信这东西,有的人多一些,有的人少一些。自信的人拥有心理学家所说的强大内控力。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命运。他们倾向于付诸行动。他们敢于开拓未来。
国家亦然。有些国家有自信,有些则不然;有些曾经拥有,后来却失去了。上周,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亚历克斯·塔巴罗克在自己的博客“边际革命”(Marginal
Revolution)中,让我们对比美国在第一次冷战(对苏联)与第二次冷战(对中国)中的行为有何不同。在我看来,两者形成了鲜明反差——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带着理所当然的自信,而今天的美国虽更强大,却已失去了曾经的从容。
20世纪50年代,美国的情报部门认为,苏联在多项军事技术领域正在超越美国。随后在1957年10月4日,苏联将第一颗卫星“斯普特尼克”送入太空。
震惊之余,美国以自信姿态回应。一年之内,美国宇航局和高级研究计划局(也就是后来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)就成立了,后者催生了互联网等重大成果。1958年,艾森豪威尔签署了《国防教育法案》,这是美国在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改革之一,加强了在数学、科学及外语方面的人才培养。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增加了两倍,国防部大幅增加研发支出。短短数年,联邦政府研发总投入激增至预算的近12%(今天约为3%)。
美国领导人深知,超级大国较量是军事经济之争,更是智力竞赛。比拼的是创新能力。他们用教育手段来对抗苏联的威胁,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人才优势。
历史学家哈尔·布兰兹在《暮光之战》(The Twilight
Struggle)一书中指出:“美国经济在冷战中之所以表现出色,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大学表现更出色。”从1958年至1970年,联邦学术研究资助从2.54亿美元飙升至14.5亿美元。布兰兹注意到,在上世纪早些时候,美国的大学落后于欧洲顶尖学府,到冷战结束时,美国大学已雄踞全球之巅。
如今我们身处第二次冷战。过去二...